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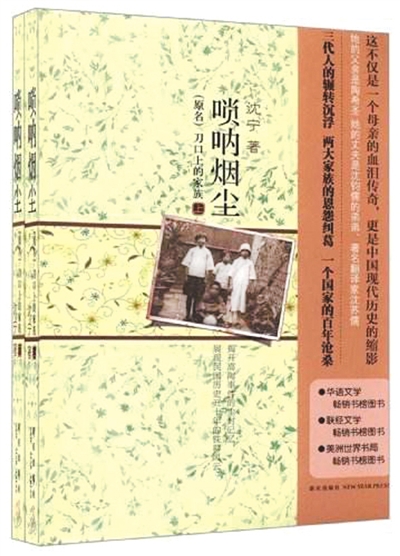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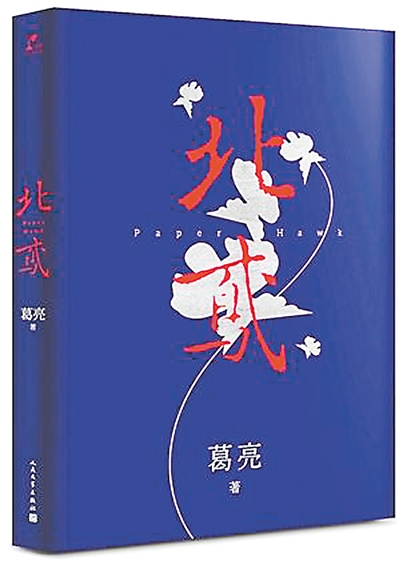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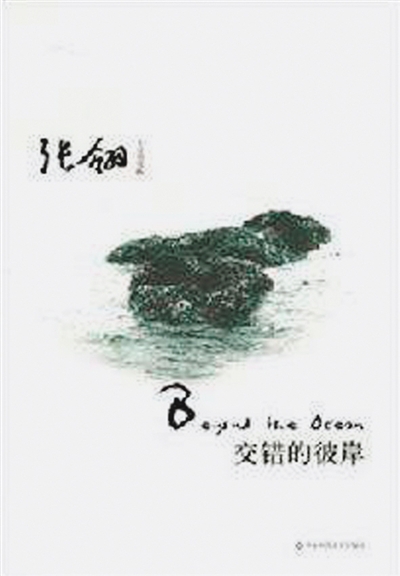

家国情怀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母题,辐射怀乡恋土、血缘追索、生存焦虑、民族复兴等创作维度。从20世纪6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至今,创作者虽适应了“把自己连根拔起栽种到异国”的文化阵痛,但原本已无比坚定的“落地生根”,却发生了再次“落叶归根”的微妙转向,随之衍生的是文化乡愁由感性逐渐让渡于理性。家国情怀可以有三重解读,即对家国的定义、对家国的感情、对家国的期待。随着题材广度与技巧精度的双向提升,家国记忆、家国情感、家国使命的传承和发展体现华文文学的新意与新变。
从“落地生根”到“二次移民”
20世纪60年代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困顿消极与渴望民族振兴的家国梦共生。海外游子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从对亲人的依恋、对乡土的回忆、对故国的热爱中播撒开来。小说酝酿起失根的困惑,流转着“日暮乡关何处是”的伤感,对母国的眷恋,更深层次目的是获得文化的认同与精神的归属。同时,留学生文学特别关注留学生群体的切身问题,以此凸显中西文化间差别的明晰性和碰撞的必然性,但陈若曦借《突围》《二胡》等作品提议“告别畸形的、分裂的家国之恨,拥有健康的、平和的中国形象及中国情怀”。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是揭示留学生失根痛苦的经典文本。丛甦是在《野宴》中较早提出了“夹缝”概念,“生活在别人的屋檐底下,屋檐虽好,终究是别人的。”她同时回答了留学生该“怎么办”:“我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书写我们的向往和梦……”
上世纪80年代的新移民文学延续了於梨华、白先勇、丛甦、陈若曦等人对隔膜论的阐发,而此时的家国梦已与个体的自我实现交织在一起。比照同时期华裔作家的英文小说,同样有对文化失根的思考,它显现为父辈(中国经验)与子辈(西方经验)之间的文化理念冲撞,进而激化现实与理想的既定矛盾。谭恩美《喜福会》中龚琳达的一段独白可与其互证:“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但保留中国的气质,可我哪能料到,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我认为,留学生文学重点在失“魂”,而新移民文学则为失“根”。前者一直坚定于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和对西方文化的防御,家国之爱是格外浓烈而痛彻的;后者立足于个体的心灵体验,以文化夹缝中的两难心态为中心,传达新移民的即时状态:渴望融入西方但无法被完全认同,于是重回中国又不能再被全然接纳,最终还是选择回归西方。而90年代新移民文学代表作家张翎从中国故事起步,信奉写作这一行为本就是一种对故乡的回归,依据自己的青少年经历实施对江南记忆的重构,又将成年经验凝聚于北方叙事中再造。
21世纪以来的世界华文小说持续对家国的关注,但思考点已实现新的着陆:从海外处境/想象中国的思维范式,转为现时问题/现实中国的思路结构。从某种意义上看,视角的变化与创作者的频繁“海归”密切相关,他们得以直接融入中国现实生活,亲历中国新变,故而对家国的体验不再是来自记忆或经验,而是源自真实当下。薛忆沩在《希拉里·密和·我》中提供一个论点:“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它让移民的人永远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那么,对于海归作家而言,故乡与异乡是辩证的,中国具备故乡与异乡的双重特性。他们是在场的旁观者,具有更自由的审视距离和更从容的观察视角,于是他们对家国的表达,可以从原先的情感攀援直击入现时的问题解决。《空巢》(薛忆沩),解析城市空巢老人为何成为电信诈骗主要受害群体的原因;《垂老别》(张惠雯),揭露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人伦的崩坏,揭示失去土地的农村老人因其无用性与无利性反遭子辈遗弃的悲剧;《佐敦》(周洁茹),刻画内地女性移民在香港面对的生活窘境、身份歧视、家庭畸形。“香港的天,就比乡下的蓝吗?阿珍看不出来。”现居香港的阿珍、阿芳却与60-80年代欧美世界“边缘人”处境不期而遇。
从家族溯源到家庭记忆
家族谱系构建是“家”的重要呈现方式。家族的代际传承是最基本叙事线索,与门风、乡土、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组合体,目的是反观社会问题与人性问题。考察华文文学的家族小说,如《交错的彼岸》《唢呐烟尘》《海神家族》《金山》《北鸢》,家族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展示的平台,深耕于文本的家国情怀,以家族血缘为点,以种族血脉为面。
张翎采用地标式的家族建构,即聚合家族流变史、个人成长史、文化发展史,将温州梦与他国梦谱系化和具象化,例如在《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里,形成西方望族与江南世家的中西呼应。而《金山》是她的家族叙事的阶段完结篇,最显著的文学价值是用现代汉语为“长眠在洛基山下的孤独灵魂,完成一趟回乡的旅途”。小说以洛基山与开平碉楼共同装载方氏家族的家国梦,方锦山、方锦河、方锦绣,托起“山河锦绣”的家族祈愿,包裹海外华人怀乡的浓酽和还乡的企盼。沈宁的《百世门风》探讨的论题是,在现代社会中该如何保留和传承中华文明的血脉。它侧重家族文化内涵的开发,以沈钧儒和陶希圣的家族谱牒为本,细数沈、陶两家历代传承的三大精神遗产:感恩、书生的傲骨和独立、明确的是非观念。2016年葛亮的《北鸢》,也是延续类似的节奏,设计卢文笙与冯仁桢两条家族叙事线,以家族文脉昭示民国风骨。
近年来,世界华文小说对“家”的塑造主动规避集体经验的叠加,格外专注个体家庭的事件与心理,以中国故事为叙事背景,收缩宏大的家族叙事,转而书写变动不居的普通家庭沉浮。《陆犯焉识》是严歌苓以祖父严恩春故事为小说蓝本,检视陆焉识、冯婉瑜与命运较量几十年中历历在目的跌宕唏嘘。张翎在《流年物语》里将全家放置于不同年代,由不同的机遇与处境撞击出刘年对自由的各种形式探索。李凤群的《大风》详述张家每一代人的寻根行动,重新定位个人与乡土的关系:“倦鸟总会归巢,而我们却将一去不返。”戴小华以《忽如归》为家人立传,诚恳记录戴家故事,视沧州“镇海吼”为精神旨归,阐明“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秉持并坚守“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价值观。
当前世界华文文学对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越加重视,家国情怀追随着“落叶归根”/“落地生根”中空间与身份的动态转徙,产生理念与理解的变化推演。家国情怀的持续性与新质性,彰显了海外华人文学创作者不停歇的文学想象力与不中断的社会使命感。(戴瑶琴)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