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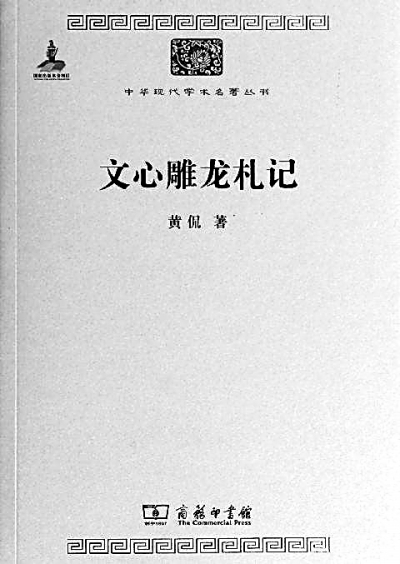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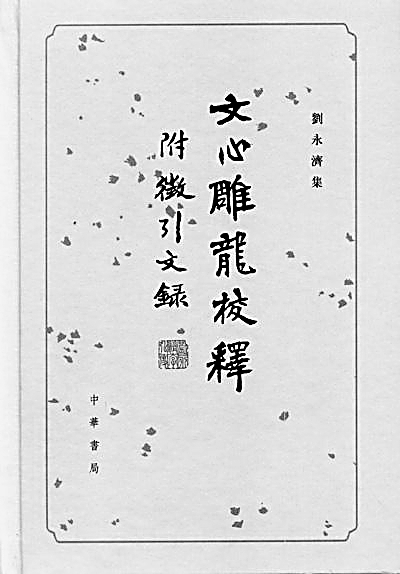

资料图片
《文心雕龙·章句篇》称“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刘勰认为,文字是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是人们说话写文章表达思想的依托。“练于骨者,析辞必精”(《风骨篇》),“缀字属篇,必须练择”,“趣舍之间,不可不察”(《练字篇》)。《练字篇》更是刘勰所撰“汉字批评”的专论,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相关问题。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练字之功,在文家为首要。”用字之要,文家无人不晓。刘勰认为,练字之方要从文章整体出发,用字要雅正,反对怪异字眼。诗文是有机整体,字则是这个生命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刘勰正是从文章整体来谈用字的。比如“兮”“夫”“之”“乎”等语气词,看似“无益文义”,却起着“语助余声”“弥缝文体”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闲字。在这个意义上说,一篇文章也要“得一字之助”(《章句篇》)。刘勰认为,文章是否有“风骨”也与用字有关。他主张用字要扎实而不能移动,避免浮泛,所谓“捶字坚而难移”,这样才有“风骨之力”,如果“瘠义肥辞”,则是“无骨之征”了。(《风骨篇》)
用字关系到文章的结构布局,结构密实的文章,增一个字减一个字都不行。“字不得减,乃知其密。”西晋时期,谢艾和王济的文风一繁一略,但他们的文章“繁而不可删”“略而不可益”(《镕裁篇》)。正因为文字不能随意增删,所以修改文章也不容易,所谓“易字艰于代句”(《附会篇》),改一字比重新写一句还难。当然,文章高手却能通过更换几个字使文章大放光彩。三国时,中书令虞松受命作表,一再修改,景王都不满意。钟会大笔一挥,只改了其中五个字,景王连连称善,可谓“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也”(《附会篇》)。
刘勰认为,诗文用字,要因人因情因体而异,所谓“辞者理之纬”“理定而后辞畅”(《情采篇》),“情与气偕,辞共体并”(《风骨篇》)。字是有情感的,“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夸饰篇》)。欢乐的场面,每个字都好像在笑;悲苦的情境,字音如泣如诉。单看字眼、听字音就可以知道作者的喜怒哀乐。刘勰又说:“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字音不协调的文章,犹如口吃,是为文病,所以作家要“剖字钻响”(《声律篇》),也就是要研究字的声韵。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较早认识到文字的情感功能。后世的诗词理论较多地论及,如清代词人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叙论》说:“阳声字多则沉顿,阴声字多则激昂。”早在齐梁时期的刘勰就指出了这个道理,相比之下,我们就知道刘勰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了。
刘勰说“诗书雅言”(《夸饰篇》)、“字以训正”(《指瑕篇》),诗文是雅道,所以遣词造句一定要雅正,粗俗字眼是诗文大忌。刘勰称虞夏文章是“万代之仪表”,因为它们“辞义温雅”(《才略篇》)。对于那些用字不雅的文章,刘勰会提出严厉的批评。比如《谐隐篇》云:“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把应玚的鼻子比作“削卵”,把张华的身体比作“舂杵”,语言丑陋,是不道德的。中国是礼仪之邦,遣词造句要讲究礼义,有违礼制的文章难免遭人诟病,高才如曹植也不能幸免。《指瑕篇》指出,曹植是“群才之俊”,但其《武帝诔》说“尊灵永蛰”,其《明帝颂》说“圣体浮轻”。“永蛰”“浮轻”这样的词是不合礼制的,因为“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
古今文人皆有好奇之心,所谓“爱奇之心,古今一也”(《练字篇》),但用字如果一味追新逐奇则会变成诡异。刘勰反对诗文用怪字、生僻字。如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作文以“以奇字纂训”(《练字篇》)、“诡势瑰声”(《物色篇》),到三国时读起来就有困难了。刘勰称这样的文字是“字隐”“字妖”。文字离奇,整个文章读起来难懂,风格也怪异:“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练字篇》)刘勰又多次批评晋宋文人追新逐奇,所谓“近代辞人,率好诡巧”“逐奇而失正”(《定势篇》),“采滥辞诡”(《情采篇》)。一味“空结奇字”则必然成“纰缪”(《风骨篇》)。文章用字要以思想内容的表达为根本,抛弃奇诡文风,文章才能归于正道:“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练字篇》)
有意思的是,刘勰说的练字,不仅要从思想内容着手,也要注意字体本身的审美。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认为,刘勰这是要求“精语必得美字以达之”。用字如何追求“形体美”?刘勰认为须革除四弊:“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练字篇》)所谓“诡异”,就是“字体瑰怪”,如曹摅诗:“岂不愿斯游,褊心恶哅呶。”其中“哅呶”两字诡异。“联边”即“半字同文”,半边相同的字在文章中常常“龃龉为瑕”,用多了则成“字林”。“重出”即“同字相犯”,同一字在句中重复出现会相互抵触。“单复”即“字形肥瘠”,笔画简单的字(瘠)联结成句,显得支离稀疏;相反,笔画繁杂的字(肥)联结成句,则显得密集晦暗。只有繁简字错落有致,“参伍单复”,这样的句子才会“磊落如珠”(《练字篇》)。注意到字体繁简与文章美丑的关系,这是刘勰的卓识,扣住了汉字形象性特点,也与当时的文风有关。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认为:“刘勰重视字形的选择,有着汉字特点和当时骈文昌盛两方面的原因。”
刘勰的“汉字批评”,其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不仅用之于创作理论的体系构建,亦用之于批评鉴赏的具体实践。刘勰文学鉴赏论的核心范畴是“六观”;而六观其二便为“置辞”,足见汉字批评在刘勰鉴赏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经典作品的用字,堪称后世文学的典范。刘勰认为,《诗经》用字生动,桃花、杨柳、出日、雨雪、黄鸟、草虫本是自然界寻常物,《诗经》分别用“灼灼”“依依”“杲杲”“瀌瀌”“喈喈”“喓喓”这些叠字来描写,就写出了它们的“鲜”“貌”“容”“状”“声”“韵”,妙笔生花,“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达到心物一体的艺术效果。这样生动的字眼,“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物色篇》),虽经千百年也不能替换,可谓历久弥新了。《春秋》是儒家的经典,刘勰多次肯定其“简言以达旨”的用字特点,称其“一字以褒贬”(《征圣篇》)、“一字见义”(《宗经篇》)、“褒见一字”“贬在片言”(《史传篇》)。
对于各式文体,刘勰多一言以蔽之,精准地概括其文体特点。如用“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弘深”“巧丽”等字眼来概括“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符檄书移”“史论序注”“箴铭碑诔”“连珠七辞”等文体的特征。(《定势篇》)
在作家作品论中,刘勰也常常运用整体浓缩性的表述,虽为片言只语,却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精妙传神地把握住作家作品的艺术神髓。如“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明诗篇》),分别用“雅”“润”“清”“丽”四个字表述张衡、嵇康、张华、张协四位诗人的风格特点,简约而精准,无须多言,读者对几位作家的人格魅力、作品风貌就心领神会。刘勰评《古诗十九首》“直而不野”(《明诗篇》),“直”和“野”两个字,看似矛盾却辩证统一,既有诗学的审美维度又有诗教的伦理维度,纪昀认为此评切中汉代诗歌的“佳处”。这种对文学的印象式整体把握,妙在直入主题,把握住了对象特质的主要方面,一语道破其中的奥妙。
对于历代文风,刘勰尽量用一两个字来概括,如《通变篇》用“淳而质”“质而辨”“丽而雅”“侈而艳”“浅而绮”“讹而新”,来概括黄唐、虞夏、商周、楚汉、魏晋、宋初等历史时期的文风,既有阶段性的精准描述又涵括文学史的历史演进。对于文学鉴赏,刘勰也是一语中的。《知音篇》开篇说:“知音其难哉!”一个“难”字,看似稀松平常,却道出文学鉴赏的种种奥妙,所以纪昀称这个“难”字是“一篇之骨”。《文心雕龙》的汉字批评,举重若轻,以简治繁,一言穷理,以少总多,将丰富繁杂的文学现象浓缩为三言两语甚至一个词或一个字,一字千金,境界全出。
钱锺书《谈艺录》说诗文是“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诗文说到底是由一个个字结成,是文字的艺术性组合。纪昀称《文心雕龙》“辨字极为分明”,刘勰“汉字批评”的理论及实践,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作者:吴中胜 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