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文艺,是大地的事业,是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文艺工作者只有扎根生活的土壤,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把生活琢磨透、理解透,才能创作出激荡人心的作品。这是文艺创作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民日报约请六位名家讲述他们五年来的创作心路,结果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对大地、对生活,都有着孜孜不倦的探寻与思索,他们把自己的文艺生命与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创作因而不断焕发新的光彩。今天,本版专辑推出六篇文章,借此祝贺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在京成功召开,并祝愿中国的文艺事业蓬勃发展,从高原迈向高峰。
——编 者
做坚硬的小石子
李雪健(中国文联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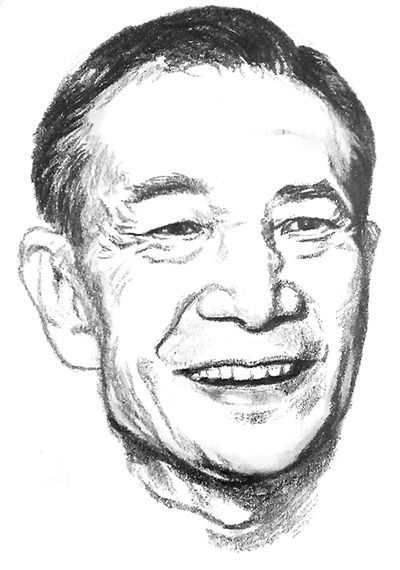
5年,一晃而过。2011年11月2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我被大家推举为副主席。得知这一消息时,我正在电影《一九四二》的拍摄现场,很是意外。这个荣誉很重,我的心里一直不踏实。
比这个荣誉更重的,是2014年我作为文艺工作者代表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身为一个老百姓、一名演员能够参与其中,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参加座谈会等于在我的头顶罩了一个光环,也戴上了一个“紧箍咒”。这是比文联副主席、影协主席更重的光环,更紧的“紧箍咒”。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你尽心了没有,努力了没有,作品是最好的证明;是否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这份信任,观众会给出最终的评价。我是一名演员,创作是我的本职工作,除了再接再厉做好本职工作,无以为报。
这5年,我的作品能让观众有些印象的有6部。电影《一九四二》里我饰演中华民国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电视剧《人活一句话》里演了上世纪20年代的县令,电视剧《有你才幸福》里演退休工人祺瑞年,还有电视剧《嘿,老头!》里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刘二铁,《少帅》里的张作霖,电影《老阿姨》里的甘祖昌将军。此外,还有没播出的电视剧和一些龙套角色。生病后再接戏,我给自己定了四条标准:一是剧本好;二是我能完成;三是剧组是一个敬业的团队、尊重艺术规律;四是不重复自己。这些作品满足了我的心愿。
用角色与观众交朋友是我的追求。这5年,从观众到文艺创作者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化,我在创作中也有一些思考。文学艺术产业化、商品化,就像老龄社会一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遇见的新情况。文艺不可避免地要与经济发生联系,但艺术创作必须动真格。方方面面都尊重艺术规律,才可能出来优秀的作品。有不少观众喜欢《嘿,老头!》,这部剧仅剧本改造就用了8个月。
观众也在变化。调查说现在的电影主流观众平均只有二十二三岁,我们的创作必须考虑这个现实。5年前电影《杨善洲》“遇冷”让我反思:观众为什么不爱看“主旋律”。在《老阿姨》里,我们努力塑造鲜活的英雄形象,展现他们普通人一样的酸甜苦辣,有不少年轻观众给这部电影点赞。电影是没有“主旋律”和“商业片”之分的,所谓“主旋律”是我骨子里就想拍的电影,但光喊口号、说教、概念化,人物不真实不鲜活,观众肯定不会买账。
作家用文字,音乐家用音符,歌唱家用声乐,演员用表演,文艺工作者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都是“心灵的工程师”。如何做好这个工程师?创作者自己的心灵要美,才会有美的作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提升自己。这是每一个人从事、参与文艺工作的责任,是每一个人心里的一根弦。
在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没有谁是局外人,也没有谁是旁观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奠基“中国梦”的“小石子”。我愿意做一粒坚硬的“小石子”,认认真真搞创作,好好为观众服务,拍出更好的戏奉献给大家。(记者 任姗姗采访整理)
留住我们的乡愁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

这些年我主要做两件事,一个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一个是传统村落保护。近来尤其是把精力放在后者上面。这里面千头万绪,有太多的实地调查与资料整理工作需要做,很辛苦,但是也很有收获。我们的团队奔走在田间乡野,所从事的工作,是个细活、苦活、不会吸引太多目光与掌声的活儿,但也是接地气的文化工作,是富有时代与历史意义的大事,是这一代文化人义不容辞、必须要干的活儿。因为不管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还是传统村落保护,都处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之中,它们随时都在变化,随时都可能失传或消亡。因此,我们的工作确实是在“与时间赛跑”,等不起也拖不起。
前两年我遇到一件事。在浙江的绍兴与宁波之间,有一个山间小村落,因为要修水库蓄水,整村都需要搬迁。那是一个古村落,里面甚至有不少宋代的文化遗存。那里的老百姓对村子感情特别深,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把村里的好东西都搬出来了,连老树都挪出来了,还在村中挖了几十袋子土作纪念。村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将村子里遗存的文物登记留档,房子绘图造册,然后在政府提供的新土地上,一砖一瓦,把“老家”照原样盖起来。听说这件事之后,我的内心很震撼,真是被他们感动了,我认为这就是写在大地之上的实实在在的“乡愁”!老百姓对自己家园的感情,比海都要深。这也是我们做传统村落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后来,我们的学术团队跑到山里去帮村民搞调研、做测量、复建村落。这不仅仅是帮助他们留住日常生活的场景,更是帮助他们留住自己的文化传统,留住对我们民族身份的记忆与认同。
现在,我国已经公布了四批传统村落国家保护名录,入选村落达四千多个。估计最终大约有五千个左右传统村落进入国家保护名录。对于这些传统村落,政府将会给予政策与资金的大力支持,使它们成为传承文化、留住乡愁的实实在在的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保护这些珍贵的传统村落,其实就是保护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
近两年来全国文艺环境迅速好转,文艺各领域都呈现风清气正、欣欣向荣的局势。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我们的文艺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讲话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我认为,这是对当前文艺界不时浮现的过度市场化与低俗娱乐化倾向的有力反拨,是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妥善处理好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关系,是提醒文艺工作者不能淡忘文艺工作的责任与担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毕竟,只为钱的艺术是没有前途的,文艺如果过度强调市场,会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物欲化,文化也会因此失去高贵的品质,真正触动人心的优秀之作势必难以出现。如果一个民族的文艺沉溺在享乐式与快餐式的氛围之中,这个民族的文艺,乃至精神,都是振作不起来的。只有当艺术家摒弃浮躁之心,拒绝名利诱惑,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精品力作。(记者 张 健采访整理)
只写熟悉的生活 叶 辛(中国作协副主席)

最近这五年里,我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客过亭》《问世间情》和《圆圆魂》。有的作家说,《客过亭》为中国知青文学画了一个圆,因为写到了步入晚年的知青的生活。《问世间情》是以长篇小说的形式,首次涉及了现实生活中的“临时夫妻”现象。而《圆圆魂》则从还不曾有人切入的角度,写到了历史人物陈圆圆的归隐去向。
乍一看起来,三本书的题材完全不同。其实,只要读过这三本书,都会知道,这三部书的写作,全和我熟悉的上海及贵州的生活有关。知青生涯使得我总是对上山下乡那一代人分外关注,我笔下的知青,往往生活在山乡、在西南、在我熟悉的贵州村寨里。《客过亭》里写到的重返第二故乡的老知青们,目的地也是山乡里的客过亭。而在《问世间情》里,小说中人物所工作的单位,他们组成的“临时夫妻”家庭,其男女主人翁,也都是来自于山乡进城的打工一族。我甚至还可以透露,动笔之前,我数次去体验生活,召集座谈会的大型工厂,就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贵州民营企业家开的。
那么,《圆圆魂》呢?也和贵州有关?有人要说了,这可是历史人物啊!
但确实也和贵州有关。
因为30多年前史学界有过一场争论,使得我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关注:陈圆圆这位引起历史众多话题的女性,是否确实归隐在贵州偏远蛮荒的大山深处?我搜集争论双方的文章和材料,我实地去往岑巩县马家寨,我找来了几乎和陈圆圆、吴三桂有关的所有书籍、演义、小说和民间传说。而当2014年新华社发出消息说,经过国家明清史专家多次考察认定,陈圆圆的归隐地确实在贵州岑巩的水尾镇马家寨,我受到启发和触动,找到了晚年陈圆圆归隐心理这样一个角度,写出了长篇小说《圆圆魂》,还被爱好历史小说的出版社推出了手稿珍藏录音本。
梳理这五年来的创作历程,无非是想说一句:我只写自己熟悉的和体验过的生活、有感悟的生活。2013年贵州建省600周年,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编选了一本散文集《叶辛的贵州》,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数十年来,我为贵州写下了约摸80万字的散文、随笔、小品一类的文字,我从中挑选了35万字的文章,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又从35万字中精挑细选了18万字,推出了这本书。在这本以《插队生涯》《村寨忆往》《黔山贵水》《情系山乡》四辑组成的散文集中,字里行间无不告诉读者,贵州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文学创作的精神原乡。正是在把贵州不断地与上海进行对比观照中,我拥有了两副目光看待都市和乡村,故而时常有灵感冒出,总有新的生活形态激起我的创作热情。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古今海龙屯》也是这样一部书。
生活在上海,时常地去往贵州,在沿海和内地之间捕捉生活的新意,感受新的时代风貌,这就是我五年来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形态。
这样说不等于我不往别处去,深入上海的社区和乡镇,在祖国的各个省市区采风,甚至为参加《孽债》英文版的首发式去澳洲——只要不呆在书房里,我愿意去感受和体验,积极到生活中去,力争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
悲悯情怀大文章 曹文轩(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

文学圈子有它自己的时尚,大众文学更是如此。时尚成了一望无际的灿烂的花田,人们犹如采蜜之蜂蝶,嗡嗡然飘飘然趋之如潮,唯恐那花田于瞬间烟消云散。甚至我所一向关注的儿童文学也不能幸免。某些光怪陆离的卡通、故作痞子状的少年写作,一副反叛面孔、一口野蛮腔调、一股深秋凉风的某些网上文学,吸引了成千上万双纯净而又充满好奇的眼睛。这些图画与文字,最大功能就在于让那些涉世未深的孩子陷于欢乐的疯狂。应该看到,相比从前,人们虽然少了温饱之虞,但也失去了心灵的丰盈和目光的深沉。在一片缺乏意义的傻笑之中,人的心灵变得苍白,目光变得短浅。
也许,文学可以让人们安静下来。而能够让人们安静下来的文章,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都应该有悲悯情怀做底子,是与天地共存在的感动文章。
悲悯情怀(或叫悲悯精神)是文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我以为,任何一个古老命题——如果的确能称得上古老的话,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才被称为文学。文学有一个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具备的特殊功能,这就是对人类情感的作用。我们一般只注意到思想对人类进程的作用。其实,情感的作用绝不亚于思想的作用。情感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部分。如果一个人仅仅只有思想——深刻的思想,而没有情感或者情感世界比较荒凉,是不可爱的。
而以上所言,正是文学可以让我们安静下来的理由。
当我们打开一本真正感动的书,我们会停下匆忙的脚步。一个拥有文学的人,乏味的生活在他眼中或许可以换个样子。一个拥有了文学的人,他的行为有了弹性,语言有了意蕴,做任何事情,都会在一种境界里,总有一份难得的雅致与高贵。这个生命,远离庸庸碌碌的平凡格调和低下的审美趣味,无论短暂还是长久,它的质量都是不可预测的。我在奥克兰做演说的时候讲到文字的意义,我说:你可将文字视为葱茏草木,使荒漠不再。你可以将文字视作鸽群,放飞无边无际的天空。你需要田野,于是就有了田野。你需要谷仓,于是就有了谷仓。文字无所不能。
也许,我对文学的理解始终也不会是流行的。我的处境,我的忽喜忽悲、忽上忽下的心绪,常常会让我想起儿时在田野上独自玩耍的情景——
空旷的天空下,一片同样空旷的田野上,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穿过几块稻田,穿过一片林子,走过一汪水平如镜的池塘,走过一座细窄摇晃的木桥……
就这么走着走着,忽然看到芦苇叶上有一只鸣叫的“纺织娘”,我先是一阵出神的凝望,然后将右手的三根手指捏成鸟喙状,弯腰缩脖,双眼圆瞪,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但就在微微张开的“鸟喙”马上就要捉住它时,它却振翅飞走了。于是我只好用目光去捕捉,捕捉它在阳光下飞过时变成精灵样的身影——一小片透明的绿闪动着,在空中悠悠地滑过,终于飘飘然落在大河那边芦苇叶上。我望见先前那片单薄的芦苇叶空空地颤悠了几下,不由得一阵失望,但随着“纺纱娘”的叫声怯生生地响起,我的心思又在不知不觉中游走开了……
这些年来,总有这少年在田野上的感受:兴奋着,愉悦着,狂喜着,最终却陷入走不出的寂寥、孤独,甚至是恐慌。然而这不就是文学的魅力吗?就像田野的魅力一样,文学不可抵挡地迷惑了我——更准确地说,那些文学理念还是迷惑着我,使我无法自已。
对于我而言,我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幸福,就是回忆起它们时那种乡愁一般的感觉,而这就是文学。
故事隐藏在路上 阿 来(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
有时,我怀揣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形诸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
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或自己的书中呆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怕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这些年,我的四本书,或者我写的四个故事,就从这两种不同方式得来。
四年多前,写完了取材于藏族史诗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在有关史诗材料的寻访过程中,听到了另一个历史故事的不完整的民间版本。为求证回头便去读清代史料。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是今天四川西部的一个县。把这块小地方的有关史料从浩繁的清代史料中一一打捞出来,足有上百万字。这些文字促使我不断去回访那个地方,一段废弃的古道,一座河上曾经有过的桥梁,三四千米雪山上已然消失的关隘,一段曾经有上千人殒命的峡谷。然后,继续搜集梳理新的史料,然后,再重返现场,从当地人口中听取那些口头的传说,自然也有当地人稀少的文字记载。两年多时间,在故纸堆中和故事现场的不断往返,终于使我在第三年写出了非虚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
写完不久,我依然去往青藏高原。这一回,没有准备,只是想去看见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现实。五月,高原地带草色刚刚返青,四处残雪斑驳。有些时候,往高处攀登,雨变成雪。有些时候,从高山牧场去往低处农耕的峡谷,雪又变成雨。在路上,总遇到一些本该在上学的少年。他们从山上下来,在路边向来往的车辆摇晃着手里的东西。停下车,他们会拿出一块奶酪,一块小动物的毛皮,更多则捧出刚从雪线附近的草坡上挖出的虫草:“虫草,虫草,三十元一根,三十元一根。”我熟悉这些孩子,如果是秋天,他们捧在你面前的会是几只蘑菇。但现在,他们只是说:“虫草,虫草。”这天,我停下车,问一个孩子,打算用这些钱干什么,他说:“给姐姐买跟同学一样的东西。姐姐在城里上学,要有跟城里同学一样的穿戴。”这句话击中了我。那天,我改变计划。在当地县城一个稍微舒适的酒店住下,打开电脑,写这个新遇到的故事,故事叫做《三只虫草》。我想,我要用清新的笔调写一个善良的高原少年。我要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天真少年在今天这个消费社会中的历险记,而且,我不能让他在这个社会中沉沦与迷失。
这个故事使我意识到,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其实还可以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自然界到底能在什么程度上承受人类无休止的索取。沿着这个思路,我又写了《蘑菇圈》和《河上柏影》,揭示这个消费至上的社会的种种图景,揭示环环相扣的商业链条对自然界,对乡村,对弱势群体的剥夺。
这是我近五年所写的四本书的缘起。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更是关于社会的。对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惟一方法。
大地传奇讲不完 张 炜(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地区是我长期写作和生活的地方,她给予我心灵上永久的支持和鼓励。我曾用二十余年的时间,实勘了半岛的百余座城镇村庄,跋涉在海边、大山与河流之间,完成了450万字的“大河小说”《你在高原》。长达22年的书写与行走,几乎使我倾尽心力。接下来的五年需要重新出发,也正是母亲般的半岛让我再次背起背囊,恢复起初的力量。
大地故事讲不完,她的现实与历史有无尽的蕴藏等待挖掘。展开时间的皱褶,深入光阴的沉积,就会焕发出心底的激情和感动。在这片时而灼烫时而冷肃的土地上,诗人尽可以沉湎和歌唱,用吟哦给梦想镶一道金边。我用《半岛哈里哈气》讲述孩子们的喜乐忧伤,与稚童一起歌唱。在这段崭新旅程中,我的心中装满希冀,接连写出了《少年与海》《寻找鱼王》和《兔子作家》,它们都是奉献给少年的礼物。
美丽的半岛是老革命根据地,以盛产黄金和水果闻名于世,春秋战国时期曾为富裕的齐国腹地,属于拥有渔盐之利、最早掌握了丝绸与炼铁技术的强大东夷族。李白向往的居住了仙人的瀛洲就在这里,诗人游历之后,感叹“烟涛微茫信难求”。古往今来因为财富争夺、寻仙问药,这里终成为一片传奇的土地,上演了无数悲喜剧,令人唏嘘。
这里是道教圣地,也是佛寺最多的地方;在近代,基督教最早从此登陆,于登州西部建立了医院和学校,西方文化影响渐巨,以至于成为四大宗教对抗融合、新文化运动激烈博弈的前沿地带。半岛怀麟医院早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创办的协和医院二十年;新学崇实学校的学子由青岛分设机构转往上海圣约翰大学,并由此留洋,后来又催生了齐鲁大学。辛亥革命北方最重要的策源地也在这里,北方同盟会支部即设于此,下辖北京天津东北三省新疆陕甘广大地区,主要领导人徐镜心即为龙口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常常提到的“南黄北徐”,“南黄”是黄兴,“北徐”却很少有人知道是徐镜心。
徐镜心是孙中山的战友,共同于日本发起了中国同盟会,归国后身负重要使命,发动革命,组织大小起义无数,最后被袁世凯杀害,年仅四十岁。孙中山一生仅为一个企业家题过词,即烟台的张裕葡萄酒酿造公司,因其老板系南洋首富,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巨大资助,被誉为“革命党的银行”。
作为半岛人,常要面对这里的“神迹”与“血迹”,为一代代奋争者而感泣。徐镜心好比革命党人的一把锋利宝剑,他后来被追认为“革命大将军”。他的半岛战友牺牲甚多,如王叔鹤就被凌迟于龙口。还有走向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大批崇实学子,都不该被忘记。
为一代奋斗者书写,记下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法推卸的责任。历史已经远去,但纪念却是永存的。在这纪念中,我们尤其不应忽略一些核心地带的核心人物。只要打开了那部封存的历史画卷,我们就会听到振聋发聩的人喊马嘶。
半岛多么瑰丽,半岛多么伟大,半岛多么神奇,半岛上有一些倔强的心灵。在近五年中,我费时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写出长期酝酿在心中的长篇小说《独药师》。(制图与人物速写 蔡华伟)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