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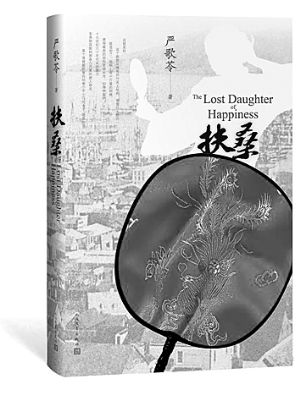
严歌苓目前已经将《扶桑》改编成了剧本,但具体拍摄计划还不确定。

▲ 对于读者认为严歌苓近期出版小说的故事没有突破性,严歌苓表示小说是写给自己的,不在意读者看法。
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必须得接,好莱坞打来的,需要我马上答复。4日下午,记者赶到作家严歌苓入住的国际俱乐部酒店时,她的上一个专访接近尾声,中间去接了一个电话。
之后是一家杂志社拍照。严歌苓在镜子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从身材上看不出她已经58岁,这或许得益于她早年在成都军区文工团的芭蕾舞训练。
现在严歌苓住在德国,但在国内她的消息不断,最近就有关于她的小说《扶桑》要被改编成电影的传言。3月5日,严歌苓和高晓松在北大以糟糕的历史与优美的文学为题展开对谈。《扶桑》是我创作中期一部很重要的作品,但它在大陆的传播不够广泛。接受专访时,严歌苓表示这也是时隔20年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该书的原因。
被一张中国名妓的照片打动
《扶桑》的创作过程也像一部小说。
1993年的一个中午,严歌苓等丈夫劳伦斯吃饭。她在附近的楼下看到一个箭头指向中国移民博物馆。那是一个在地下室的陈列馆。我看到一幅巨大的画像,画像的中心焦点就是一个盛装的、身形比较高大的中国妓女。她看上去还有那么几分的端庄。她的周围围着很多的人,人群中的几个白人对于这个妓女流露出一种狐疑的神色。这个妓女带有某种秘密性、象征性。严歌苓说。
照片中的女子被称为一代东方名妓。
我深深地被她身上的气质打动了。严歌苓仍能清晰地记起那幅给她极大冲击的照片。
我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按图索骥一路寻找过去,最终她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女人的名字。
但寻找的过程中,她对中国移民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44年才解除的排华法案中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务工的华人不准带家属到美国。他们也要有家庭生活,也要解决生理问题,所以妓院就应运而生了。严歌苓在史料中发现,大概有三千个女孩子被贩卖到那里,妓院开在唐人街,开在各种在建铁路的沿线。
上述移民史博物馆照片中的中国名妓就是这三千女孩子的一员。这些妓女在解决华人的生理问题之余,还吸引了很多白人的小孩。
当时旧金山男女比例是40:1,有资料记载,这些妓院吸引着大概有2000个白人男孩的定期造访。所以这是一场东西方的大邂逅,我决定要把这个写出来。严歌苓说。
彼时,35岁的严歌苓到美国已经五年,她原先身上小有名气的军旅作家的光环早已被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无情地粉碎了。
资料中找不到照片上的女人,严歌苓就从小说里找。
她给这个女人起了一个名字扶桑。
有研究者表示,作为一个东方人置身于西方世界多元文化价值体系中,是极度敏感而脆弱的。所有尖锐的疼痛投射在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半世纪前北美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将严歌苓体会和理解的东方伦理和盘托出。
简单讲,《扶桑》的故事是这样的:克里斯一生中致命的吸引,就是从12岁开始迷恋20岁的她扶桑,一个被贩卖至美洲的中国性奴。屡遭通缉的大勇(男主角之一),有个从未谋面的新娘,与扶桑相遇,他失去了寻找真相的勇气。
出版社在书页上写道:扶桑,不小巧的女子,她经历的一切,就像是苦难的代名词。这是一部关于十九世纪北美洲移民浪潮的史诗性作品。
《扶桑》当年的发表过程也值得一提。创作《扶桑》时,严歌苓只身涉过重洋,到美国攻读艺术硕士学位。其时她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常常处于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中,完成之后她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后来她看到台湾《联合报》征文启事,遂以一个无名的写作者投稿,竟意外地斩获第一名10万元大奖。如果没有这次贸然投稿,《扶桑》的手稿也许会和她的好多成品半成品一起被塞在地下室里,永不见天日。
扶桑对整个东方世界具有高度的象征性
坐在记者面前的严歌苓优雅从容,很难想象她之前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我刚到美国,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学校的电梯一样的挤,我嫌别人,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热汗蒸着我,连自己都嗅出一身的中国馆子味。我总是徒步上楼,楼梯总是荒凉清净,我总是在爬楼梯之间拿出木梳,从容地梳头,或说将头发梳出从容来。我不愿美国同学知道中国学生都这样一口气跑十多个街口,从餐馆直接奔学校,有着该属于牲口的顽韧。
《扶桑》的主人公是一位妓女,她总是从容甚至带点麻木地张开双腿接受一个或者多个男人,书中也不乏这样的句子:(扶桑)她跪着,再次宽容了世界。
然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琼花在《扶桑》中看到了一部残酷的移民血泪史,东西方两种文明、两个种族之间曾经对立、猜忌、误解的历史。
在她看来,扶桑笨拙雍容的体态、慈憨寡言的心性、饱受摧残的经历,对近代东方世界具有高度的象征性。琼花指出,这部小说不是简单地描写血仇,恰恰是通过扶桑所表现的无边的爱与宽宥,来呈现不同文明与种族间的差异性、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重性。惟其如此,对这部小说和其中的人物才产生了多种解读甚至误读。
你没法打倒一个不反抗的人
■ 对话
东方早报:为什么起名字叫扶桑?
严歌苓:这是一种误解。有一句话叫此去扶桑东更东。扶桑一层意思是比东还要更东的一个地方。古典神话中也讲到扶桑是生长在很东边的一棵树,太阳就是从扶桑树上面升起来的。还有一个就是扶桑是一种四季植物,它是仙人掌花的一种,一百年才开一次。它生长在墨西哥的西海岸,就是我们坐船一直往东走,最先遇到的一个海岸,所以起名扶桑是有一种象征意义的。
东方早报:作为第五代移民,创作《扶桑》时,你与劳伦斯结婚三四年。书中扶桑与克里斯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产生的近乎宿命的误解,你在爱情及婚姻生活中是否也曾遇到过?
严歌苓:这个当然会有的。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非常吃力,这个时候也只能不求甚解了。
东方早报:如果从《扶桑》剥离出一个抽象的灵魂,你觉得这个小说是关于什么的故事?
严歌苓:关于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她就像所有中国女人一样,她可以吃所有苦。扶桑其实是很存在主义的,她认为你可以来爱我,只是来平等地爱我就好。你不要来救我,我也并不需要你来救我。不要像西方对非洲,动不动就要来救。几千年来,东方人就是这样生活下去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有力量的、有道理的、有逻辑的。
就像你让扶桑脱去了红色的外衣,等于就离间了她与她生命中本身的环境、生态的最后一丝维系,它像脐带一样连接着它的母体,母文化与自己。
东方早报:我看扶桑,觉得她特别憋屈,有那么种逆来顺受的感觉。
严歌苓:你觉得甘地逆来顺受吗?他的不合作和扶桑的不反抗是一样的。你永远打不倒一个不反抗的人。其实强奸这个词语包含着歧视。相比而言,这个词语带来的伤害可能更甚。
扶桑她是对事不对人的。包括那次被强奸,扶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
东方早报:扶桑总是微笑,她从不对任何人表示出明显的爱憎。故事中,你盛赞扶桑身上的带有神性的古典式的善良与隐忍与母性的光辉,如果扶桑可以靠着接受与容忍自我救赎,为何她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自己理想的爱情与生活?
严歌苓:她把这两个男人都玩儿了,最后自己能够全身而退。两个男人最后的结果也并不是非常好,反倒是扶桑,用婚姻的形式把自己保护了起来。
东方早报:扶桑以那样的姿态去接受男人和世界的时候,甚至都让人感觉到她是冷漠的。
严歌苓:你有没有看过《钝感力》?按照这个理论,扶桑一点儿都不冷漠。她被抓起来了,她说我是贼,她想要自由,这样就可以去找她喜欢的人。
东方早报:叙事技巧上,让一个几乎全知的叙事声音不断地判断与评价,将主人公扶桑置于一个失语状态,为何这样安排?
严歌苓:我写一个故事是一定要有意思的。我没法儿接受那种枯燥的、只是在历史中挖掘这个人物,我是一定要把她拉到我眼前的,活生生的,以和她可以对话的这种方式去呈现。
东方早报:你被改编的作品有很多。
严歌苓:因为故事性比较强。
东方早报:你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如《天浴》《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哪一个是你觉得改编得比较成功的?
严歌苓:《天浴》吧,比较接近我的原著。改出来我还是能够接受的,比较像我的作品,我的风格。萌生这个小说也与陈冲有关,我们比较近,我是看着她一步步拍出来的。
东方早报:会不会想要改编《扶桑》?
严歌苓:我已经改编成剧本了。一个好莱坞的制片人很感兴趣。还要经过进一步的审核,很多内容应该是要割掉的。
东方早报:从《金陵十三钗》到《少女小渔》《扶桑》,为何偏爱写这种边缘化的、弱势的群体?这种有些刻意的新奇感是否会消解文学与思想?
严歌苓: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弱势群体,或者说女性就是弱势群体。我自己也是比较接受和隐忍的人,所以为什么不写我自己认同的人。
东方早报:有人说你最近的创作没有创新和颠覆,尤其是《老师好美》和《床畔》。
严歌苓:讲故事和讲故事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写不出《床畔》那样的作品。
东方早报:你如何看待作家与批评家的互动?
严歌苓:我其实不在意读者怎么想的,可能因为离得远,也听不到什么声音。我是写给自己的,写给自己的才彻底真实。
东方早报:你觉得自己成功吗?
严歌苓:我很满足。我觉得挺成功的。我有一个稳定的家庭,还有女儿。
(文章部分内容参考庞建丽:《论严歌苓本土题材小说中女性的身体书写》、严歌苓:《海南边》、琼花:《〈扶桑〉:一部文学经典的再传播严歌苓、高晓松、史航对谈〈扶桑〉与十九世纪北美洲华人移民潮》谨致谢忱。)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